洪兴故事五——肃反“白雀园”(上)
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后,社团的局面颇有些危机。
在外面,收拾完各路军阀的蒋介石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洪兴社身上,对几个苏区的围剿迫在眉睫。当然,这一年9月开始的一系列中日军事摩擦又给了各个苏区生存和发展的时间。
在内部,城市工人运动的牌基本已经打光,随着罗章龙、何孟雄这帮人的被捕、被开除,城市运动的骨干也损失严重。社团手里只剩下几个苏区这点“正资产”了;而这些正资产也有很多问题。
这些苏区,说是有十几个军的番号,但其中真掌握几个县作为固定根据地,拥有财政体系、兵员支持,能提供军事医疗、人才教育,正规军队人枪有一万左右的也就三个——江西的朱毛彭,鄂豫皖的曾中生、旷继勋,湘鄂西的夏曦、双刀将。其他的苏区和部队,基本就是流寇性质,被追到哪里就打到哪里,没有根据地,只能靠流窜打土豪(杀富济贫)为生。
这些可怜的小苏区给中央的信件都是要资源的!大到医药器材、无线电器材、军事装备;小到望远镜、指南针和手表;当然军事干部(打仗用)和政治干部(管理地方、为部队收集资源)也都要。
可中央自己都靠几个大苏区定期送金子维持生活,俄国总部提供的本金和追加投资养活总部领导们都不够,哪里能支持他们呢?还好,手里有些干部资源可以送过去。
斯大叔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,当年看到有实力的冯基督,枪炮、人员就滚滚的送;现在自家的崽饿的嗷嗷待哺,他也只是从总部派些懂马列、有技术的人回来帮忙。
对大鸾他们这些社团管理层来说,继续在上海的办公室吹空调、写报告、发指示,于社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给不了现在社团唯一的正资产——苏区以物质上的帮助,那就把自己和苏联来的“白领们”派过去帮忙吧。而且,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风波,管理者们也希望能够更接地气。
在三月初解决了刘邦“富田事件”的纠纷后,大鸾提出了一个把中央和领导们安置到苏区的具体计划,并经过政治局通过:
——1、中央政治局前往朱毛彭的江西苏区,大鸾、向忠发、张闻天、秦邦宪、王稼祥带队过去,和之前已经到岗的项英、刘伯承搭建新的管理层,代替当地的“独裁者”刘邦。
——2、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苏区分别组建中央分局,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。张国焘、沈泽民、陈昌浩去鄂豫皖掌控;夏曦在湘鄂西负责。可以说把社团的管理层分三处存放,三个中央都有对辖区内社团、政府、军队的绝对控制权。
——3、上海留一个中央分局,直接向江西的中央政治局汇报。
那位问了,刚成功上位,而且马上因为向忠发被捕而担任社团一把手的王矮子呢?人家回莫斯科总部做洪兴社代表去了,继续喝咖啡、吃大列巴。

(社团高层这次大分手后,在延安才重新聚齐。)
三月底,张国焘带着“28个半”里的三位高手——沈泽民、陈昌浩、张琴秋(沈泽民的夫人)一行四人,在社团最核心的特务顾顺章的安排下,分两路去往鄂豫皖。

(张琴秋的故事,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单独讲给大家。她不会想到,这次同行的三个男人,都和她产生了深刻的爱恨情仇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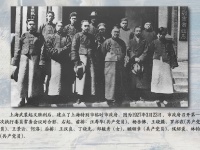
(后排中间戴礼帽的这个就是传奇特工顾顺章。他送了张国焘后,就留在武汉表演魔术,随后不幸被捕。他的被捕引起一大串连锁反应,其中一条就是加速了上海总部逃亡。)
鄂豫皖苏区展现给张国焘的,并不是一幅欣欣向荣、可以大展宏图的画面,而是矛盾重重、危机四伏的困局!
第一个难题,分散。无论是行政上的鄂豫皖苏区,还是军事上的第四军,都不能算做一个整体。
鄂豫皖苏区是在大别山的三个苏区基础上逐步发展组成的——鄂豫边、豫东、皖西。大家虽然有联系,但相互之间却有颇多聚乡自保的农民组织(民团),甚至被地方军驻屯的县城阻隔。等张国焘他们来的时候,皖西和豫东基本能连接在一起,形成以金寨为核心的一块苏区;鄂豫边这里,形成以七里坪为核心的一块苏区。
三个小苏区起源于三场不同的暴动——黄麻起义(接下来我们会接触到的组织者有吴光浩、戴克敏、徐朋人、徐子清、徐其虚、郭述申、郑位三、王树声),商南起义(接下来我们会接触到的组织者有周维炯、漆德伟、戚海峰,未来最有名的是16岁就跟着杀富济贫的小鬼洪学智),六霍起义(风云人物少,但反而活到社团上市的将军很多)。三场不同的暴动又催生了四军来源不同的三支部队——1师、2师、3师。

(大别山三场起义和他们产生的苏区位置大概如此。河南、安徽、湖北三个省交接的三不管地带,大别山恶劣的地理条件,是苏区存在的基础;七里坪和金寨是两块苏区的核心。这块穷乡僻壤诞生了社团上市后最多的将军。)
四军的来源除了这三支大别山本土部队外,还有一支1930年鄂东各起义部队组建红八军攻打长沙(这也是社团对“立三主义”控诉的重要内容)时散落下来的部队。这帮散落下来的鄂东农民兵挂着个“15军”的番号游荡到了鄂豫皖,于1930年底和鄂豫皖的部队合并成了红四军。
苏区被分割的问题是力量散,形不成统一的地方支持系统,物资、人员的输送都会受影响。且都是小根据地,自身防护能力弱,和白军、民团经常拉锯战,管理不稳定。
军队来源不统一的问题更大。打仗是件靠信赖的事,父子兄弟几个人狠下心,肯定能打跑十几个临时编队的小混子。一个单独发展,从几十人的小队伍混到上千人的军队,自己内部有信赖,但和另一支部队合作就有障碍。
而且,这里还存在一个历史问题——小小一块大别山被三个省划分,不同区域的人天生就有你是湖北佬、我是荷兰帮、他是安徽人的心态。省份矛盾不经意间就贯穿到苏区和红军中。
举两个例子:
1929年9月,第二次“豫鄂会剿”中,鄂豫皖3个师都被从根据地打跑,在大别山流窜作战。徐老蔫率领的31师(黄麻起义发展的,后改为1师)和周维炯率领的32师(商南起义发展的,后改为2师)在麻城北部首次碰头。实力强的31师虽然客气的给了小兄弟一些子弹,但徐老蔫也很谨慎的要求战士们枕着枪睡觉,并和32师宿营地做了安全防范。双方合作打了一仗后,32师也悄悄的不辞而别。虽属同门,但明显缺乏足够信任。
30年9月,整编后的1师、2师又合作向平汉路进攻。打广水时,定的计划是徐老蔫带1师从北边打,2师在军长许继慎的带领下在南边打。结果2师按兵不动,搞得仗没打赢,徐老蔫帐下最得力的营长高汉初也牺牲了。为此,老蔫少有的发了脾气,作为一个师长,把军长许继慎一顿臭骂。
分散已经很麻烦了,但还有第二个难题——外来干部持续加入,管理层不断调整。
最重要是党政干部。一开始地方上最大的领导是鄂东特委负责人、黄麻起义领导者之一、本乡本土的干部徐朋人。30年2月,大鸾又派出郭述申统一三个地区特委为鄂豫皖特委,担任一把手。六届三中全后,30年10月,大鸾又派曾中生来做特委书记加四军政委。曾中生刚干了没几个月,六届四中全会后,31年4月,张国焘又来把他替代了。2年不到,总经理就换了4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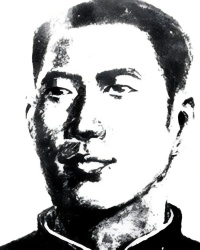
(徐朋人,黄安(现在叫红安)本地人,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。被国涛开除党籍、逮捕、枪毙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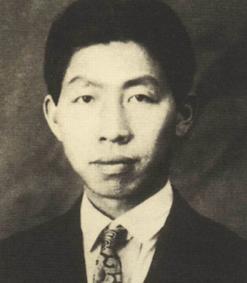
(郭述申,被张国焘打压后随徐海东到陕北迎接了中央红军。后一直在辽南发展,成为苏军驻扎的旅大市社团、军队一把手,也算是笔者祖父曾经的大老板)

(曾中生,黄埔四期生,霍光钦定“36位军事家”之一,曾希圣他哥。)
比地方干部变化更频繁的是军事干部(毕竟这是苏区更直接需要的稀缺资源)。吴光浩莫名其妙牺牲后,徐老蔫和桂步蟾(刘邦农讲所的弟子,29年战死)成为最早来鄂豫皖支持的军事干部。老蔫一直带着黄麻起义这一支的部队(31师,后来1师)。

(吴光浩,黄埔三期生,铁四军做到营长,参加了贺胜桥、汀泗桥血战。国共分裂后,回老家黄陂组织“黄麻起义”。从背景、到资历、到能力,这人才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能人。而他29年莫名其妙的被杀,也是后来肃反、仇杀的重要根源)

(老蔫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:一个人要混得好,业务能力要强,还要有高情商。)
30年3月,郭述申来整合鄂豫皖的地方党政工作;一起来的许继慎负责整合鄂豫皖军队。许继慎和郭述申的整合是很高明的:
让实力最强的1师单独行动,且1师师长徐老蔫兼任副军长,这让徐老蔫和一师很满意。
许继慎自己作为军长,主要带2、3师行动,又把2师(来源商南起义)的本土扛把子周维炯安排去更弱的3师(来源六霍起义)做师长,提拔周维炯的表哥漆德伟做2师师长。这样,2师的枭雄们很满意。3师之前经常跟着2师打仗,服周维炯,也能满意。
最后,让在鄂豫皖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曹大骏做军政委,稳定了局面。

(许继慎,黄埔一期生、叶挺独立团的营长,叶挺24师的团长,这个资历足够硬;安徽六安本地人,回老家带队伍,背景足够强。打仗和政治都有一套。但和徐老蔫明显的区别是此人太精明、自负、霸气、浪漫,业务能力强而自控力太弱。最终成了肃反的导火线和牺牲品!)
1931年1月,流窜到鄂豫皖的15军(彭大将军8军残部)和鄂豫皖部队合并为4军时,又带来了三位军事领导:旷继勋、蔡申熙、余笃三。
这次的分配就很明显的是强龙压地头蛇了。刚来的旷继勋直接代替许继慎成为4军军长,刚来的余笃三直接代替曹大骏做了政委。部队整编成两个师,10师师长蔡申熙来自弱小的15军;老鄂豫皖底子只剩下11师师长许继慎;徐老蔫被踢出去做了参谋长。

(川军老将旷继勋,从新来的张国焘,到鄂豫皖的老底子徐老蔫、许继慎,大家都不喜欢他,都说他没本事。最后,成为内斗的牺牲品。)

(蔡申熙,黄埔一期生,北伐的营长、团长,曾经是双刀将的部曲。国涛到鄂豫皖后和其相处不错,成为国涛非常倚重的军事人才。可惜战死。)
外来干部多、管理层不断调整,带来的问题就是矛盾多。“天大地大,人事最大”。不论地方社团、地方还是部队,来了新领导都要对老势力进行分化、瓦解,形成自己的管理班子。在这个过程中,矛盾不可避免会出现;给时间消化还好,现在几个月就变一次,前面的矛盾还没消化,后面的矛盾就累加上。
再结合第一个问题——鄂豫皖地区本就有三大派系。于是,时间和空间的矛盾又堆积和纠缠到一起。鄂豫皖这么个小公司,却有着极为复杂的人事斗争。
第三个难题,苏区生存压力大。
四周都是“正常”社会(所谓正常,是所有人都能忍受,我们不讨论是否公平公正);维持一个“反正常”社会,确实太难了。当时的各个苏区,普遍面临内外各三个压力。
外部三压力:正规军,民团,黑社会。
正规军不但在苏区周边驻扎,苏区中的县城往往也作为据点被正规军控制。比如,张国焘已经进入鄂豫皖苏区,在向政府所在地七里坪进发的途中,还能遇到驻扎在黄安城(黄麻起义的核心城市,现在叫红安)的萧之楚部44师的一旅人马。多亏护送的独立团打“麻雀战”才成功通过。
民团也很好理解。大别山区自古以来盗匪横行,老百姓习惯了以大户为核心、以氏族为纽带、以村舍为单位,据族驻寨自保。有时候盗匪强悍了,几个村镇联合自卫,这就成民团了。打家劫舍的“反政府”武装与民团是天生的敌人。
(李大人当年凑淮军老本钱,就是向师傅曾国藩学会的,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源把家乡各家族、各村镇能打的团练集中起来使用。)
当时的情况——红军去白区打土豪(杀富户、抢财产),政府军就来打苏区,民团跟进报复。红白双方对抗强烈到什么程度呢?看当事人回忆:“他们对于反抗租债捐税的乡村,房屋烧毁十之五六;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乡村,房屋烧毁十之八九。在黄安七里坪地方,出农民不意,绑了150多人,不管男女老少,一概施以最惨烈的死刑,有的剖心挖眼,有的用烟薰,有的切指头,有的截足杆……。国民党说我们杀人放火,其实杀人放火最凶的而且最残忍的,仅只有国民党军阀。我们红军除了杀豪绅地主以外,简直是非常平和的。”
以七里坪为核心的鄂豫边苏区,和以金寨为核心的皖西苏区,就是被强大的民团势力拦住的。
这里从闹长毛开始,就养成了自发保境安民的习惯。村民们在族长、士绅的带领下,住山上的就直接利用地势筑山寨,住平原的就挖护城河筑水寨子。这些山水、寨子,不但束缚了苏区的发展,还收留了苏区打土豪后逃难的农民,影响了苏区的人口。危害极大。
不要小看这些土农民山寨、水寨的防御能力。31年4月,曾中圣和最强的师长徐老蔫因为一时意气,强攻民团山寨,就损失近千战士。
这些民团中的翘楚,就是被红军战士们称为“顾半城”、“顾狗子”的顾敬之。这是位在四方面军几乎所有人的回忆录中都会提到的杀人狂魔。
“顾狗子”在外见过世面,了解洪兴社的套路;回乡后坚持“二五减租”(农民地租降低25%,农民借贷利息不能超过20%),以化解洪兴社的宣传口号影响力;又自己花钱买了300多条枪组建民团,以保境安民;在家门口广场设断头台当众砍杀叛徒奸细,以严明法制。“顾狗子”既不允许官军、匪徒随意进入辖区,也坚定地和红军干。
“顾狗子”的战术不是传统筑寨子,而是照搬红军的游击战术——红军大部队来打,他就带着乡亲们“跑反”躲到山里;红军一撤,他就带人马出来打。结果就是和红军形成势均力敌、互不侵犯和平局面。
“顾狗子”保护的清区,一直是两块主要苏区无法连接到一体的绊脚石。一直到15年后,麻城的后生王树声、金寨的后生皮定均再次从老家新建的解放区撤退——也就是著名的“中原突围”时,老对手“顾狗子”还给了他们很大威胁。
讲到这里,说个好玩的事:话说张国涛通过“顾狗子”地盘,从鄂豫边苏区到皖西苏区指导工作时,王树声的团护送国涛路过一个茶棚。当地的百姓因为红军到来,都已经“跑反”到山中躲藏,可这个茶棚的老头却继续做生意,大家就知道是“顾狗子”的侦探。于是团政治部主任就和老头开诚布公的谈话:“快去报告顾大老爷,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,只在休息地喝水造饭,不会损害一草一木,叫他不要留难;否则,当心我们的报复!我们是有名的30团,全部在此!有枪800多根,重机枪4挺,不要讲错了”。然后才顺利通过,临走时,“顾狗子”的民团放了两枪,算是大家打招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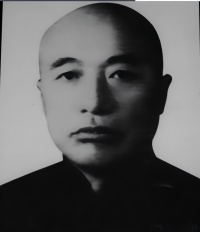
(国涛评价“顾狗子”的清区游击民团区域:“农田遍地、道路平坦、桥梁坚实、房屋完整”,一幅欣欣向荣之气。顾狗子后来担任商城县长,大力发展教育,对抗日寇,还推行其“保境安民”那套“丑恶理论”,因此和蒋家的独裁政府也矛盾重重,并被判刑。解放后逃到台湾。)
除了民团,苏区还要面对一些怪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,其中最主要的是——红枪会。这是一个和“洪兴社”抢基本盘的组织。据说根源于“白莲教”、“义和拳”的“红枪会”,与民团用同族、同乡为纽带结合去保护家园不同;他们只要是穷哥们都可以参加,目的在于扩张、抗租、劫掠。
除了土生土长,没有外来强大理论支持外,“红枪会”基本就是“洪兴社”在农村路线的翻版。这半地上、半地下的组织是民团和政府之前的重要对手;现在更猛的洪兴社来了,几家就放弃前嫌、合作御敌。而对于和自己套路类似,竞争基本盘的“红枪会”,社团也是绝不客气。
1929年底“罗李会剿”时,徐老蔫的战术就是安排群众们“跑反”躲到山里,自己带着人马和敌人绕圈子,然后抽冷子打相对弱的“红枪会”。五战五捷打垮了红枪会的一支较大力量,俘虏头目戴五爷后,老蔫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万人公审大会,当众镇压(杀掉)戴五爷和其头目。借此,向群众们高调宣布自己和“红枪会”不共戴天,老百姓要跟只能跟“洪兴社”。

(底层工人抱团取暖就是青帮、洪门,底层农民抱团取暖就是红枪会一类。所以,红枪会和黑社会是洪兴社在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对手,不可能共存。)
除了外部压力,更可怕的是内部腐蚀。主要是三个:“AB团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改组派”。
先说“AB团”,名字是“反布尔什维克”(Anti-Bolshevik)的缩写。这个组织,最初是北伐打下南昌后,学生领袖段锡朋找些同学、老乡组建的。目的是帮蒋介石对抗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正宗与洪兴社联盟。手段主要是选举时大家心齐举手;群众运动时组建、联络自己的群众对抗汪精卫-洪兴社联盟的群众。
后来还是洪兴社先动了粗,1927年4月2日(就是412反革命政变前10天)洪兴社的群众武装占领了江西国民党部,打跑了段锡朋,抓了AB团骨干。
后来,这个“AB团”组织在国民党内也没了声音,段锡朋老师换到教育行业工作,还曾担任小龙人母校的校长。但“AB团”这名号却在江西留了下来,而“AB团”在江西的一些“同志”还继续反赤。正好猪毛在江西搞社团,国民政府安排探子、杀手进来办事,安排说客进来策反堂口兄弟,这帮由国民政府安排来搞破坏的家伙逐步就被冠以“AB团”称号。
在江西,和“AB团”有关的最有名的是两件事:一个是“富田事件”,刘邦派李韶九去部队抓“AB团”,结果逼出了叛乱。二个是黄埔三期生,刘邦在农讲所的同事、一起秋收起义的铁杆,红一方面军第一任参谋长朱云卿,在医院被加入“AB团”的院长暗杀。
政府派去中央苏区的密探多,派去鄂豫皖也不少。对付这些敌人的斗争就是“打AB团”。贫穷年代,没什么科学侦查手段;战争年代,讲究快刀乱麻。为此,牵扯冤死的人也就不在少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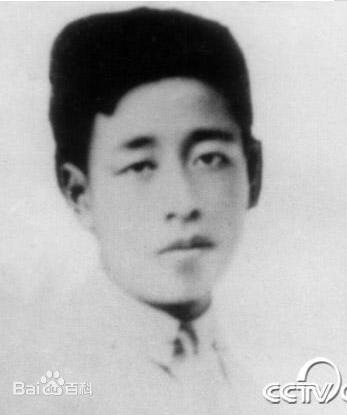
(朱云卿,从资历到能力,此人不死,一直做总参谋长,可能社团管理体系会更顺畅)
“AB团”是必须肃清的对手,可还有比AB团更讨厌、危害更大、更难查出的“第三党”、“改组派”。
世界上本就没有非黑即白的事,现实中各种情况非常复杂。以大革命时期而论,国共内部都有不少思想分支,其中尤以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影响巨大。
“改组派”来自国民党。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内讧细节,我会再开章节介绍。大概的情况是,国民党正统的两支——汪精卫、蒋介石,一个偏左一个偏右,分掌党、军;为挣权,汪系和属性相近、关系密切的洪兴社,野心勃勃的唐生智、张大王走到一起;蒋系和胡汉民、甚至西山会议派,以及最能打的广西七军走到一起。
在双方多年的互动夺权中,长时间弱势的汪精卫团队办了一件事——由核心成员陈公博组建“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”(也就是“改组派”),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员,军事上拉拢新军阀(李白、吕布、老西、富二代、唐生智等等),以对付老蒋。1930年,张大王、唐生智、石友三的陆续叛乱,中原大战李、冯、阎的合作,背后都有这个组织的运作。

(洪兴社一大成员,大汉奸陈公博,在国共斗争、国民党内斗中,始终有着重要的地位。)
提着脑袋、吃着红薯在大别山、井冈山、洪湖这些破烂地方吃苦受罪、杀富济贫的洪兴社骨干,基本都是蒋介石不共戴天的仇敌,这帮人的信仰和蒋介石也完全不可能共存。但汪精卫的“改组派”就不同了,内部很多人过去都是朋友,曾经一起做群众工作;“改组派”推行的孙大炮“新三民主义”也是洪兴社很多成员接受的思想。没啥仇恨,关系不错,思想差不多,对苏区的洪兴社干部来说,选择跟“改组派”合作也是一条可以接受的道路。
类似的还有“第三党”。大革命失败前后,国共内部真心支持合作,又颇有些理想主义的一些人就凑到一起。大家一方面反感蒋汪的争权夺利,背离“革命”宗旨,而和地方豪绅、老军阀合作,成了新“统治者”;另一方面,也反感洪兴社越来越强的民粹暴力倾向,以及被莫斯科国外人掌控的现实。于是相约组建“第三党”,自己玩,走一条真正革命的、民族自有的、平和的道路。
这派人物的名头都极大。比如国民党大佬邓演达,比如洪兴社大佬谭平山。

(谭平山,一大时的起始党员,广东分社的组建者,社团中央委员;国共合作时洪兴社驻国民党代表团一把手,任国民党组织部长,同时期刘邦代替汪精卫做国民党宣传部长,南昌起义主席团主席。)
著名学者郭德纲曾说“同行才是最大的冤家”。坚定的洪兴社人不会 投降蒋介石和他的联盟,但对于朋友转化的“改组派”,自家亲戚转化的“第三党”却会有倾向性;而这种存在于人心里的倾向性又难以调查。这些组织也确实通过朋友、同乡、同学、同事的关系联络苏区的干部,这就给各个苏区带来了巨大麻烦。
艰苦的环境下,要生存和发展,组织必须从内到外坚定一致。于是,反“第三党”和“改组派”就成了各个苏区需要完成的工作。社团对这两派早有定性:“改组派”是和国民党一样的反动派,“第三党”是孟什维克,都必须干掉!
第四个难题,组织成员彪悍。
虽然我已经说了苏区太多的苦难,但还没完!如此困难、残酷的局面下,能杀出几千带枪战士,横行乡里的苏区骨干领导,都是彪悍异常、桀骜不驯之辈。
这些人可不好管理,我举两个例子。
先说“黄麻起义”的基础人物王树声。26年,正在麻城中学读书的20岁小青年王树声就参加了农协,搞起了“打土豪”、“减租减息”的活动。可27年武汉政府一分共,搞农协的同志们就只能“跑反”,躲到大别山里避难。
“87会议”后,社团鼓励报复、组织起义。当时的社团还比较幼稚,宣传上口号激烈冲动——“平分土地”、“杀尽土豪劣绅”;而组织上又很混乱。于是,各支队伍拿着梭镖乱冲,但敌人枪一响就都跑散。
王树声这一队“起义军”算是不错的,面对夏斗寅部在麻城的正规军,还能存活下来。但最后也只剩下18个人,其中9个洪兴社成员,9个跟风加入的土匪。
一天晚上宿营时,双方9对9公开谈判,土匪提出条件很简单:“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,好好分手,否则我们就来见个高低”。王树声他们几个都是学生、农民,自然不是江湖人对手,但谈判这玩意就是要用“悍勇”博利益。大家给出的意见是“双方火并,枪一响,则正规军听到来剿,都要死;钱财你们拿走,枪弹我们留下继续战斗用”。纠缠到最后,算是谈成个折中条件——钱财给土匪、子弹交一半,江湖上以后互不侵犯。
之后,多亏了队伍中的广东老农民干部符定一提出方案——找门路去武汉买枪,大家才又有了希望。可钱哪里来呢?打家劫舍赚钱也搂不到多少,这时王树声想起了自己有钱的堂叔,便带领同志们打这个肥羊。
当大家蒙着脸、带着枪闯到人家之时,堂叔的母亲、王树声的叔祖母竟然认出了自己,并叫起了王树声的小名。这让王树声羞愧难当,最后放弃了绑架;而叔祖母则拿出了自己私藏的50个大洋和一包首饰请革命者们离开。羞愧的王树声只留下了大洋,而把首饰还给老太太。
有了钱,符定一冒着生命危险,走了几天无人的山路跑到武汉,通过自己的老乡找日本军火商人买了两支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,这队伍才重新开始发展,一直到百人规模。后来徐老蔫来到,带着队伍做大做强,这才有了一方天下。

(没有青年阶段这些经历,王树声也不可能成长为钢铁战士,甚至大将。每一个洪兴社高层成长的背后,都有残酷到极致的故事)
王树声是被环境磨练的枭悍,而周维炯则是一直的勇猛、聪颖。1924年,只有16岁的周维炯加入社团;1926年,北伐打下武汉后,社团和国民党合作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分校,18岁的周维炯被推荐去学习;1927年回乡后,因为有文化、又学过军事,就被当地民团邀请做民团的军事教官。
所谓“商南起义”,核心内容就是只有21岁的周维炯安排的一场酒局。在酒局上他把民团团长、副团长都干掉,半推半就的逼着民团的40多人跟着造反;然后结合其他几个村镇的农民组建了300多人的32师(就是那个和徐老蔫一起打仗,但互相顾忌的部队)。
周维炯打仗猛,做事也凶。和夏斗寅对抗时,国民党河南省的一个干部在商南当地还算是个地主,那就肯定要“打土豪了”。趁着此人在家,周维炯带兄弟们给他绑了起来。但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,他姓“漆”,也就是周维炯妈妈的姓氏,此人是周维炯的亲舅舅。
亲戚们拿出钱、找上乡亲们一起去求周维炯。可周维炯完全没在乎,直接安排枪毙、打土豪(财产充公)。当地为此有民谣曰“外甥作官,舅舅问斩。大义灭亲,只有共产。”这里多提一句,周维炯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其母家的亲属,我们等会还会提到。
而另一面,周维炯对于扩大队伍也是不遗余力。河南流窜来的100多土匪流寇就被他直接收编成一个团。

(年轻、冲动、霸道、不择手段的周维炯是革命的好手,但他和徐老蔫、以及徐老蔫的徒弟王树声相比,太有性格。这也是他的核心团队以后吃亏的原因,最终自己也丢掉了性命。)
第五个难题,已经具备的矛盾和仇恨。综合我以上分析的四点,残酷的环境、互不信任的合作伙伴、凶悍的作风、复杂的权力斗争……虽然因为外界强大的压力,大家能合作抗敌,但内部的小龌龊,甚至杀戮是少不了的。
“商南起义”按照社团内部的管理体系,应该由指挥“黄麻起义”的“鄂东北特委”直接领导。但当“鄂东北特委”派出徐子清、徐其虚(注意这两个人,都是黄麻起义的骨干人员)两个干部去领导周维炯的队伍时,不知双方起了什么龌龊,周维炯竟然把两个领导枪毙了!而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戴抗若也被枪毙。
然后,“鄂东北特委”又派出了“黄麻起义”毫无疑问的第一旗帜吴光浩去领导周维炯,但这位老战士竟然莫名其妙的在半路被杀。也正因为吴光浩的离奇死亡,才促成徐老蔫来大别山支持革命,成了“黄麻起义”这帮人的新军事统领。
再然后,中央特派员、特委负责人郭述申亲自来调查二徐之死,结果也差点被周维炯枪毙,有人报信才逃了一难。有了这个掌故,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何老蔫带着部队和周维炯的部队合作打仗时,野营都要枕着枪睡觉了;也可以理解社团派许继慎去管理商南、皖西的周维炯部队时,为何要专门安排手枪队护送了。
1930年10月,曾中生对鄂豫皖的红军进行混编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各个部队发展不平衡:徐老蔫带的1师(“黄麻起义”的底子)因为老蔫的善战,发展特别猛,已经有将近4000人,还有不少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;而漆德伟(周维炯的表哥)带领的2师(“商南起义”的底子,周维炯的老部队)和周维炯带领的3师(“六霍起义”的底子,也服周维炯)加起来才1800多人,还没啥重火力。
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打破各支部队以邻为壑的独立性,形成统一战斗力。这次混编,把新来的“15军”也整合了进来。
也就是在这次混编中又出了矛盾。矛盾的处理过程,给了未来的“白雀园肃反”照抄样本。
矛盾是怎么回事呢?你周维炯、漆德伟这一帮“商南起义”的当地子弟不是桀骜不驯么,不是骄傲凶悍么,不是连特委派来的领导都敢明杀、暗杀么?借混编正好收拾你!突破点就在漆德伟2师的参谋长戚海峰。
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做“山大王”,难免会有些坏习气。特委的领导们抓住了戚海峰的几个问题——“吸食鸦片,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”。并直接安排枪毙!
对此处理,周维炯、漆德伟这些大哥哥们坚决反对。但此时混编在即,徐老蔫强悍的部队在旁边把持,社团的程序正义在上面威慑,他们也就只能成为羔羊,而其反对社团决定的行为也就成了被处分的理由。
周维炯被降职为团长;漆德伟被撤销师长职位,发往上海总部再安排使用(这就是条不归路);其他一些反对枪毙的亲戚被冠以“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”罪行,而开除党籍!但注意——2、3师这帮商南、皖西的兄弟们还有个老大哥——许继慎(虽然不是起义的组织者,但老家就在当地、而且善战,已经被大家认可和接受)。

(漆德伟是周维炯的表哥,和被“镇压”的那个土豪舅舅都是漆家宗族,在武汉黄埔军校学习后回家搞革命。被撵出鄂豫皖到上海总部后,被下放到江西继续革命,31年底牺牲。死在了表弟周维炯之后。)
第六个难题,军队和地方,右倾和左倾,“军阀主义”和“立三主义”的方向之争。和企业一样,工作中的矛盾、权力上的纠纷,最终都会具象化到业务方向之争上来。苏区军队和地方的这几个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们捋捋看。
要造反,必须发动草民;要发动草民,必须满足他们疯狂的欲望。底层草莽们疯狂的欲望其实几千年来都差不多——杀豪强、分财产、不交税。社团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路数在苏区操做的。这才有大量年轻农民加入社团军队;这才有大量底层人民愿意跟着社团“跑反”,给社团做鞋、做工,成为徐老蔫他们生存的土壤。但有没有问题?
有!首先是财政问题,打了土豪、分了财产,社团部队和百姓都能过几天好日子,可接下来呢?豪强这支羊被杀了吃,还如何向他征税?造反的群氓本就穷,而且原有的税收体系崩溃,更不容易征税。
像党组织比较强的七里坪苏区一带(黄麻起义发展出来的)鄂豫边苏区,基本就没有税收的财政收入。而部队是在增加的,工作人员也在增加(仅有几个镇子和农村,却养着“财政”“土地”“内务”“政治保卫”“军参谋部”“军需处”“政治部”“军需处”“军校”“医院”“被服厂”“维修厂”等众多脱产部门……)。这些人如何养?
维持财政只能靠两个途径:1、把土豪们都抓起来,继续挖掘他们的财产,强迫其苏区外的亲属交钱(七里坪一个苏区就关了上千土豪);2、派红军到周边“白区”打草谷、劫当地土豪。
大别山那穷地方有几个“真土豪”啊?这样做的结果是苏区有点实力的家庭都被逼破产;而“白区”各阶层对来劫掠的红军仇恨极大,很难被征服,并且仇杀升级;即使无力抵抗的“白区”,在几次被劫掠后,普通百姓也都外逃,难以再筹款。时间一长,必然财政枯竭。
伴随着财政枯竭,更可怕的是社会面的饥荒。“土豪”这些先进生产者被“杀”、“抓”、“破产”,生产力降低是一定的;脱产人员越来越多,需要粮食供养是一定的;苏区打土豪的恶名和禁止投机倒把的政策,又把外地来贩粮食的商人吓跑。结果就是,苏区的粮食产量低,吃饭的人多,外来的粮食没有,内部的粮食外流。于是,整个苏区产生饥荒。
财政枯竭、社会饥荒,苏区这个公司迟早要破产。对此,不同苏区社团的党政干部们不约而同的找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——从旧秩序的破坏者到旧秩序的代替者。
具体来说就是减少烧杀,减少“打土豪”,形成持续的收税;减少平均主义的市场价格控制,鼓励苏区和外部的商业交流;脱产部队和干部舍弃“打土豪”的快乐日子,习惯过艰苦生活和自力更生,或者生产,或者卖矿;印刷纸币,学帝国主义们的套路,实现对群众的金融掠夺。
这些政策看似很好,但有一个巨大障碍:他需要苏区的稳定,不能经常被白军、民团攻陷;他需要持续扩大根据地,需要乡村管理和贸易的中心,也就是镇、县,乃至城市。但这两点是被军事干部们深恶痛绝的!
为何?首先是红军太弱,重武器少,有优秀军事技术的基层军官也少。白军来犯,最靠谱的方案只能是舍弃苏区,绕圈圈、打游击;而不能挖战壕、筑碉堡、硬碰硬。现在党政干部要我们力保苏区的稳定,这就是让我们找死!出去打仗也一样,攻击土寨、镇、县,凭现有的能力和打法太难。大家习惯的围点打援、突然袭击,目的都是抢而不是占!你党政干部要我们占领据点,就是让我们找死!
其次是实际利益。正常的财税体系下,经济主动权在党政干部手里;而游击队打土豪劫掠的方式 ,经济主动权就在军人手里。这是多大的一块权力啊!像军事干部据主导地位的金寨苏区那里,许继慎就和很多土豪家族混的非常好,经常住在他们家,并且经常换女朋友,过的很开心。当然那里的社会经济维护也不错。
说到这,我们大概理顺了发生在各个苏区的矛盾实质。大概来说(不是很细节,只说方向),军事干部都会指责党政干部“左倾盲动”、“冒险主义”、“立三路线”;党政干部则会指责军事干部“军阀主义”、“游击主义”、“流寇主义”、“避战畏战”、“右倾保守”。口号、帽子、事情变来变去,但实质的矛盾也就这个脉络而已。
好了,摆在张国焘面前的鄂豫皖苏区六大问题都列出来了。各位国师换位思考下,你们处在张国焘的位置上,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?当然 ,别和我说局面太惨淡,做的业务太残忍,完全没希望。创业本就是违背人性的事,更不要说造反这种收益极大的创业项目,成功可能性本就接近为零。要不是有张国焘、刘邦、大鸾、项英、双刀将、夏曦这种偏执型人格的家伙存在,也就没后来社团的上市成功了。
预知张国焘如何处理,且看下文分解。

